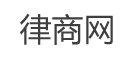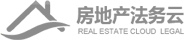2015年7月25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委员会在美丽的长沙蓉园宾馆召开《行为无效与价款结算暨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第三期依法推进会》,本律师作为全国律协建房委的一员,全程参加会议,感觉受益颇丰,现与各位同行交流,亦希望对各位律师朋友有所帮助。
本次会议除了朱树英老师及建房委的老朋友之外,官方代表主要有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高级法官关丽(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的主要起草人)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彭亚东。为了更好的总结本次会议的成果,笔者将自己对本次会议的心得与体会分为共识、分歧、碰撞与感悟几个部分与各位朋友共享。
共识
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问题,首先,大家对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形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 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司法实践中虽然也有依据《合法法》第五十二条(一)、(二)、(三)和(四)款[1]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况,但典型案例较少。
其次,对于无效合同结算问题,与会的律师基本达成一致,即:无效合同结算条款按有效合同处理,关丽法官也明确这基本上是最高院司法裁判的主流观点。根据本次会议讨论的情况,结合本律师相关的执业经验,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之所以会形成这一近似不合逻辑的定论,主要是因为如果司法实践不如此操作,基本上就推翻了整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发包人与承包人的约定归零,因为工程施工合同是以工程造价为中心的,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合同无效,结算条款也无效”,大量的工程结算纠纷将脱离双方的约定,要么以应当进入历史档案的工程“定额”为基准由审价单位确认工程造价,要么以清单计价结合工程信息价来确定工程造价。实际上,虽然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结算方式对施工单位多有不利,但是毕竟是双方合意的表示。司法实践考虑到处理这类案件的整体公平起见,只有作出“合同无效,结算条款有效”的无奈之举,颇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之意。
“合同无效,结算条款有效”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个何为结算条款的问题,即:结算条款主要是指合同中的哪些条款?按照最狭义的对结算解除,应当是合同约定的工程计价方式----工程量的确认和价的计算问题。按照广义的理解,这里可能包括付款节点、质量违约、工期延误等所有与工程结算有直接关系的条款,对于这一问题,与会的律师、法官的主流观点即应当按照广义的结算条款来处理双方的结算问题。
关于工程转包和违法分包中的非法所得没收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一条规定却基本难以适用。究其原因有是这一条规定的所谓“非法所得”,法官在具体审理案件时难以驾驭,合同无效当事人的所得就是非法所得吗?恐怕难以定论,非法所得的范围又有多大?是双方利润还是单方利润,司法审价如何认定当事人的利润?这些内容的确定可能都是司法能力范围所不能及的,所以,注定了这一条规定基本无法操作。出席研讨会的湖南高院民一庭庭长明确表示他们在司法实践中也几乎未没收过“非法所得”,因为确定难以操作。
分歧
北京袁华之律师在会议主持时给大家开了一个玩笑:出席会议的律师多是正装出席,而造价师着装较为随意,究其原因,对于工程案件100个律师脑子里面也只有对和错两个结果,而100个造价师根据自己对造价的理解,可能得出100个不尽相同的结论。工程造价纠纷确定如此,不同的工程造价纠纷造价师所作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同的,这实际上是取决于每位水平不一的造价师对定额和清单计价的套用和理解,而律师会形成对与错的定式思维则是源于司法实践更多是关心“是与非”的问题。
在会议讨论期间,就一个建设工程典型案例大家展开了讨论:北京某项目,业主方以总价包干的形式将一房地产项目承包给施工单位,合同约定地上工程按照每平方米1500元约定,根据建设面积实行总价包干,地下部分则按照700元,根据建设面积实行总价包干。从律师角度讲,这一条款约定应当是有效的,因为合同本身也是有效的,这一结算条款当然有效,按照最高院司法解释,如果合同无效,这一条款是双方的约定,也可以作为结算的依据,司法实践中基本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是,与会的造价工程师对这一约定的基本意见则是:这一约定明显不合理,应当按照工程定额来审价确定工程造价或据实调整工作价格。
本律师认为,律师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自己的思维定式,即:案情基本情况-----法律的相关规定和司法实践------本案应当如何处理。而造价师在长期从事工程造价预决算工作中,也形成的自己的思维定式,即,工程基本工程量------法定的计价依据------工程如何结算。从上述案例看,从工程造价角度看,双方地下700元,地下1500元的约定明显与工程造价的基本常识不符,从这一角度讲,造价工程理由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由于律师长期的司法训练,契约自由这一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已经难以打破,约定不公平、不合理也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在无法定变更和撤销理由,并申请法院认定变更或撤销的情况下,法官不应对双方约定的价格条款进行自由裁量。从本律师代理工程案件体会讲,律师和造价师的不同理解这一情况在具体案件中常有体现,比如说律师一般认为应当按照双方约定费率和取费标准套定额审价,而造价师则认为应当按照定额明确规定的取费标准进行计算工程量。
实际上,从律师和造价师思维的不同可以看出来,律师较为关心合法和尊重约定。而造价师较为关心合理和尊重计价规定,从司法实践角度讲,同为法律执业群体,法官无疑更倾向于律师的思维。
碰撞
相对于08清计价规范,13清单规范的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多出一些“强制性条文”,比如说,第4.1.2规定的:“招标工程量清单必须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其准确性和完整性应由招标人负责。”第3.4.1规定的:“建设工程发承包,必须在招标文件、合同中明确计价中的风险内容及其范围,不得采用无限风险、所有风险或类似语句规定计价中的风险内容及其范围。”实际操作中,是否允许发包人和承包方通过招投标文件、施工合同进行变更或排除这些所谓“强规强条”的适用,与会的律师之间,律师与造价师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主张13清单中所列的“强规强条”不具强制法律效力,承发包方可以变更或排除适用的律师理由主要是:如招标文件中规定了投标人有审核工程量清单的义务,并给予了投标人对工程理清单提出异议的程序,投标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工程量清单存在漏项或差错,则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包括工程量清单漏项的责任),即使施工合同无效,根据最高院《解释》第二条[2]的规定,仍应当参照施工合同约定来处理工程量清单漏项问题。
主张13清单中所列的“强规强条”不允许承发包方变更或排除适用的律师和造价师主要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标准化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下列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 (三)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卫生标准及国家需要控制的其他工程建设标准;………”根据上述规定,《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自2013年7月1日实施,2008版规范同时废止)为国家标准,且属于强制性标准,其中部分条款,如上列4.1.2条等属于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适用。
上述两截然不同的观点各有其道理,但本律师更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因为仔细研读《标准化法》及其《实施细则》,将工程计价方式作为国家强制性标准颇为勉强,虽然其与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有关,但是作为计价方式的基本规范等同于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标准,逻辑上有明显不通。
感悟
建设工程纠纷涉及到质量、工期、造价三大问题,法律、造价、施工技术问题交叉,建设工程纠纷的复杂性可想而知。从事这一领域工程的又多是专业人员------律师、造价工程师、项目建造师、监理工程师,各建设工程专业人员在长期从事自己专业工作过程中,对于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问题,都会有自己的专业解读,有些问题大家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如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标准应当符合国家规定,有些问题却有着各自的理解,比如说无效合同按照有效结算问题、黑白合同问题、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理解与适用问题等等。本律师认为这些理解上的分歧都是正常的,各专业人员通过交流和相关学习,才能在更多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才能对更好地解决工程施工中的纠纷有积极意义。
就律师从事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法律业务来看,多与工程造价、工程监理、项目管理等专业人员沟通,将自己的法律素养去正确合理的解释和处理工程专业问题,用法律的语言和法律的思维解释给自己的客户,解释给裁判人员,才是律师提高执业水平,最大限度地维护客户利益之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