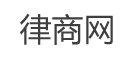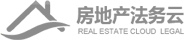案情简介:
2010年5月周某与A置业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合同约定A公司必须于2010年12月31日前将房屋交付给周某,同时约定A公司交付房屋时必须取得大产证,并在60日内协助周某办理产证。同日,周某与B物业经营公司签订了《物业委托经营合同》,约定由B公司经营该物业,为期5年。2013年4月A公司取得大产证,并于同年10月通知周某办理小产证,但办理流程中显示须与A公司签订委托经营合同,双方产生争议。周某于2014年4月诉至法院,要求解除该《商品房预售合同》。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周某遂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法院观点:
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该条规定了《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当事人一方逾期履行义务时,对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的除斥期间适用问题。本案中,周某要求依据《解释》第十九规定,由于出卖人原因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而不受一年除斥期间的限制。但法院认为,虽然A公司于2013年4月取得大产证,10月通知当事人办理小产证违反了合同的相关约定,但周某在接到通知之日起已具备了办理小产证的条件并实现了合同目的,而周某却迟迟不肯办理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依据。故驳回周某的解除合同的诉请。
律师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周某要求解除合同的期限是否受一年的时间限制。法院认为依据《解释》第十五条约定,周某的解除权因未在除斥期间内行使而归于消灭;而周某认为依据《解释》第十九条约定,因A公司原因导致周某无法办理小产证,因此其要求解除合同不应受一年除斥期间的限制。
那么,究竟应当适用哪一条更为准确,笔者认为应当先从理解除斥期间的概念着手。除斥期间是指法律规定某种民事实体权利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内不行使相应的民事权利,则在该法定期间届满时导致该民事权利的消灭。可见,法律保护该民事实体权利同时也限制该权利的实现期限,如此操作就是希望权利人能更积极地行使自身权利保护合法利益。
本案中周某所称的“A公司的原因”导致无法办证的抗辩理由无非两个:一是A公司延期办理了大产证导致周某延期办理小产证;二是A公司以先签订委托经营合同为条件办理小产证。首先,如果以第一种抗辩理由分析,A公司依据合同应于2011年7月协助周某办理小产证,周某也自2011年7月时开始享有合同解除权,解除权应当在一年内行使,但周某于2014年4月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显然因其怠于行使解除权而导致权利消灭。该分析依据《解释》第十五条,当事人延期履行情形下,对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的情形。如以第二种抗辩理由分析,笔者认为因周某与B公司签订委托经营合同在先而导致其无法办理小产证,周某可以通过司法救济途径向A公司主张履行合同。因为协助办理小产证是A公司作为出售方应尽的义务,A公司应当履行。但即便A公司不履行周某也并不因此享有《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的解除权。
《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的解除权其实是对买受人在无法办理出房地产权证、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下所使用的司法救济途径。所谓“无救济则无权利”,该种不受一年除斥期间限制的解除权是对买受人权利的最后保障,其形成条件也是法定的,即: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可见此法条保护的是合同无法实现时,受损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而在本案中,A公司已办理了大产证,也于规定期限内通知周某办理小产证,也就是说周某此时办理小产证的条件已具备,并不存在无法办理产证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因此周某不能适用该条赋予的解除权。从鼓励交易方面讲,既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可以排除,那么法院会从稳定交易的角度出发,会尽量促成交易的实现。至于周某因延期办理产证而遭受的损失,可以依据合同要求A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赔偿一定的损失。
综上,除斥期间作为一种民事实体权利的形式期限,作为权利人应当积极行使,一旦权利未在规定时间内行使,将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不管是房地产企业,还是购房人都应当在解除权具备的情况下,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否则会面临除斥期间超过后,无法行使预售合同约定解除权权利的情形。